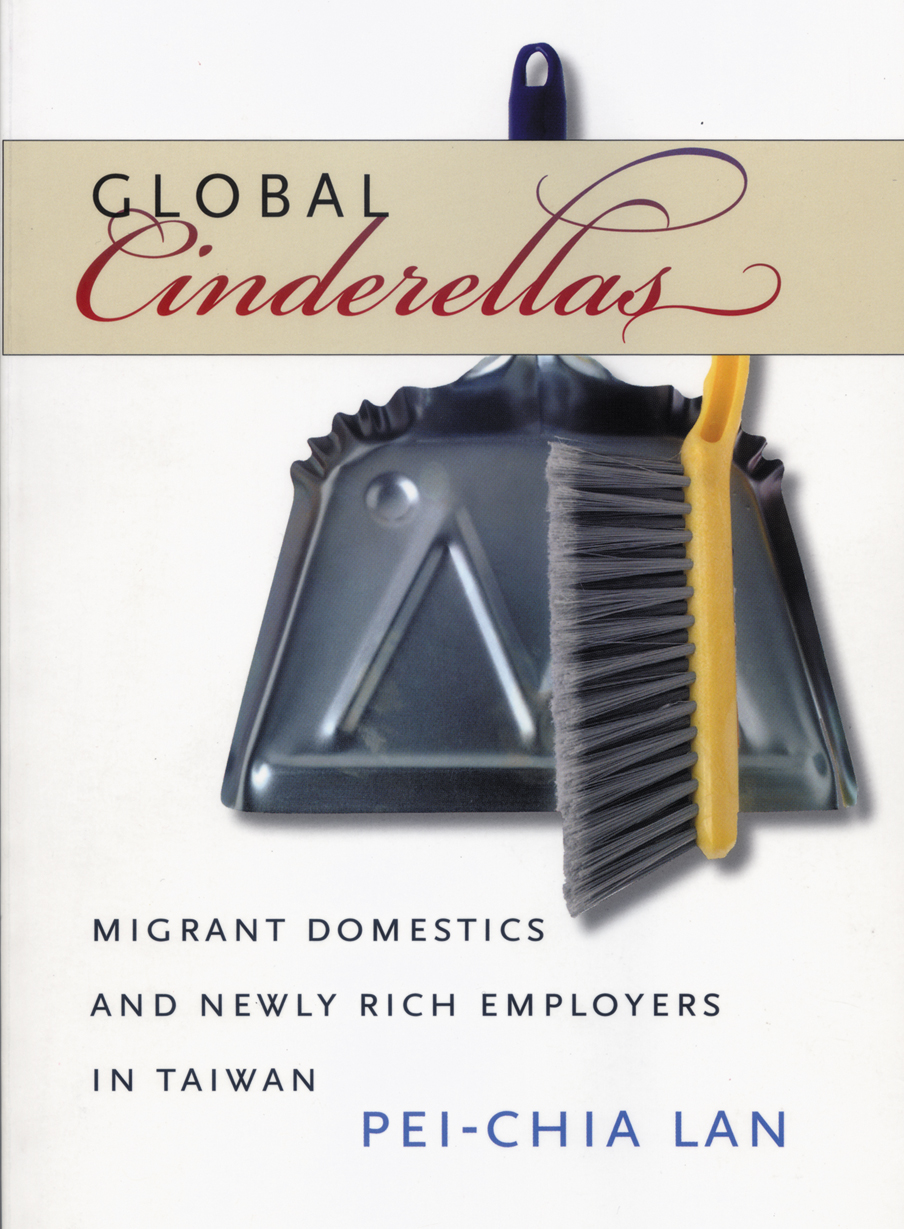
目前台灣共有超過30萬名外籍勞工, 其中有14萬為外籍幫傭與監護工,她們飄洋過海、離開自己的家庭 ,來照顧台灣的老人與小孩。絕大部分台灣人對這群人認識不多,她們為什麼來?孤獨身處異鄉的雇主家中,又遭遇到什麼?這些問題可能很多人連想都沒想過。相對於經濟起落、主權維護等「國家大事」,家務移工的人權跟流浪狗的議題相仿,從來不會成為人們的焦點;我們如何對待移工,反映的正是我們如何面對自我內在黑暗的態度。
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的最新力著《跨國灰姑娘: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》展現了長達十年的研究堅持與道德關懷。過去學界的相關論述,大都追溯家務移工單方面的跨國移動,但本書卻將新富雇主與家務移工放在同一個分析天平上,觀察兩者之間的權力互動,這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;而藍佩嘉從主奴之間微觀、精密的權力互動之「小結構」,扣連到國際政治經濟分工的「大結構」,觀察兩者之間如何相互維繫與複製、挑戰和協商,兼顧了結構力量的制約,也強調人在結構困境中籌謀出路的「能動性」,這是本書受到國際學界青睞的另一原因。本書(美國杜克大學2006年出版)獲得2007年美國社會學會「性與性別領域」傑出專書著作獎,以及「亞洲研究國際會議書籍獎:社會科學領域最佳研究」。
▓家務事難道永遠是女人事?
理解跨國移工現象的第一條線索,是「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」。僱用外籍家務工的台灣新富雇主,是隨著台灣經濟奇蹟、崛起於1980年代的第一代職業婦女、小頭家和專業人士。她們身處現代與傳統的夾縫之間,一方面,隨著女性勞動力大量進入職場,她們也追求自己的生涯、事業與成就感,視兩性平等為理所當然;但另一方面,「家務事」仍被視為是女人、母親與媳婦的份內工作。蠟燭兩頭燒讓她們疲憊不已,也讓她們身心煎熬。這些新富雇主一隻腳跨越了性別分工的藩籬,但另一隻腳仍深陷其中。剛好,全球化的經濟分工,以及勞動力的跨國移動,提供了解決之道。外籍家務移工分擔了沉重的家內勞務以及親情孝道的義務,讓新貴雇主既可追求事業,亦能滿足身為人妻、人母、人媳的責任。
外籍家務移工從決定跨國打工的那一剎那開始,也跨越了性別分工的藩籬,她們跟男人一樣肩負家計重任。但她們在跨越了性別分工的同時,也弔詭地印證了性別分工的正當性與有效性。難道不是「家務事=女人事」這項性別分工鐵律,為她們製造了跨國打工的機會?而她們即使在千里之外為賺錢受盡委屈,仍不得不時時操煩原生家庭(因為男主人通常無法克盡母職),用盡辦法做一個跨國超級好媽媽。
若根據古典女性主義的邏輯,我們應該將矛頭指向一個普遍的父權體制,同時壓迫著新貴雇主與外籍移工,男人拒絕幫忙家務是問題真正的根源。但現實中,有錢女人購買窮女人的勞動力解決問題,更可能為了滿足家務勞動的道德性質、迎合為人妻與人母的社會期待,而過度剝削家務移工。於是,「階級」因素加入,分裂了「姊妹團結」的女性主義信念。
▓主婦與女僕的權力辯證
家務外包意謂著讓不相干的外人闖入神聖、私密的家庭領域工作,打亂了公、私領域的界線,何況這個「外人」還是種族上被一般台灣人視為低劣、不潔與危險的種族。於是,重新詮釋家務的內容,區分何者適合「主婦」,何者適合「女僕」,即成絕對必要。
藍佩嘉細緻地描述了主婦的諸般「劃界」(making boundaries)行為,「勞力」的家務活動如洗衣、擦地、換尿布等,適合女僕做;「勞心」的家務活動具有表達親密情感的性質,如做菜、接送小孩、講故事等,適合主婦做。這代表了現代主婦與父權體制的「協商」,但即使如此這般「解決問題」,主婦的妻職、母職卻也因為外人代理而備受爭議,主婦們(以及婆婆們)恆常感覺焦慮、忌妒與不安全。在極端情形下,主婦甚至跟女僕彼此競爭家務能力、美貌和賢慧,男性的權威目光成為受害者之間彼此競爭的仲裁者。於是,主婦永遠不可能視女僕為一個自主勞動者而尊重之;主婦將父權體制對自己的壓迫,複製在另一個女人身上。
但藍佩嘉並不認為女僕的跨國移動只是國際經濟分工底下,純粹被動的受害者。她深入印尼與菲律賓的城市與鄉間,挖掘女僕們跨國移動的種種複雜經濟、文化因素,還原一幅幅令人動容的人性面貌,也顯示她們即使身處惡劣的環境中,也能聰慧、敏捷地行動,維護基本的權益和尊嚴。
▓跨國候鳥的漂移命運
家務移工不僅僅只是因為窮,為了錢而飄洋跨海;跨國遷移的旅程,對移工來說,既是解放,也是壓迫。有些移工(尤其是菲律賓移工)跟台灣的新富雇主殊無二致,雙肩同樣挑著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的重擔。透過跨國遷移,這些移工做著相同的家務勞動,卻從無償變成有薪。她們追求解放,卻發現自己橫渡重洋來到另一個囚室。她們也跟新富雇主一樣,在一腳跨越性別藩籬之際,另一腳仍深陷其中,仍要向父權體制「協商」如何兼顧、滿足身為女人、母親和妻子的社會期待。但是,由於階級的差異,這種「解放」與「協商」顯然是充滿著苦澀與矛盾。
外籍家務移工照料著別人的寶貝,但是誰來照料她自己的寶貝?許多移工將對自己孩子的思念「移情」到雇主小孩身上,在一個案例中,菲律賓媽媽對著自己孩子叫錯雇主小孩的名字,這段插曲,在雇主眼中,是照料服務的品質指標,但是在原生家庭,卻恐怕成為各種指責、怨懟與誤解的源起。許多移工媽媽在台灣受盡屈辱,縮衣節食,卻寧願花大錢買昂貴禮物,挖空心思彌補遠距離疏遠的親情,但丈夫卻因為男子氣概受損,而不願主持家務,甚至劈腿棄家;小孩也往往認為母親在異鄉流連享受而遺棄他們,從此冷漠以對。夾在工作與家務責任、傳統束縛與現代吸引的兩難之間無法平衡,移工往往從暫時的離家打工變成永遠的漂移。
▓外勞政策中的種族偏見
上述主婦-女僕的生命史雙重奏,更被放進國際政治經濟的大結構中檢視。台灣做為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國家,一方面從東南亞輸入低階、藍領勞工,另一方面也從歐美、日本等核心國輸入高階、白領的專業人士。然而,台灣作為一個「看不見的國家」(invisible nation),既富甲四方又不被承認,充滿了認同的挫折與焦慮,一方面感嘆國際社會的現實無情,另一方面在認同強者及渴望強者認同之餘,面對比我們更邊緣的國家,又完整複製此種涼薄無情。最能體現此點的,正是台灣移民政策和外勞政策中,對不同種族「他者」(the other)大小眼的態度。其實,「他者」往往是一面映照出自我扭曲與矛盾的鏡子。
台灣移民政策對待白領工作者,不僅沒有配額限制、可自由換工作,合法工作5至7年之後,也可獲得永久居留權,甚至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。至於藍領「外勞」,其待遇實質上接近半奴隸狀態。在配額限制之下,限制更換雇主、限制居住,更責成雇主監視外勞、防止逃跑的責任,幾乎剝奪所有經濟與社會權利,當然也不可能獲得永久居留權。
這種體制的主要特色在於防止移工與本地社會發生長久關連,成為社會一員。其目的即是在享受移工年輕、便宜勞動力的好處之餘,拒絕付出勞動力更新的成本(譬如受傷、生病與衰老),將之推給移出國承擔。但歸根結柢,此一體制更立基於某種害怕跟低劣種族(永遠是東南亞民族、卻不是白種人)混合的想像恐懼。
本書作者生動地呈現了外籍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之下的生活、慾望與感情,從而在一個商品化的冷酷壓迫世界中,還其一個人性的面貌。做為新富雇主社會的一員,我們有一個機會,可以同情地理解其處境,認可她們的貢獻,支援她們爭取尊嚴與基本公民權,從而也讓我們自己從性別、階級與種族的多重桎梏中解放出來。
